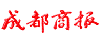世界杯> 新闻> 德国> 世界杯1/8决赛德国VS英格兰> 正文
厄齐尔:我们会击败英格兰 英媒回击:这是年少轻狂
“这属于一个孩子的年少轻狂。”英媒《太阳报》昨天回击德国球员厄齐尔(土耳其裔)的口出狂言。这个刚刚失去祖母的小伙子用土耳其人的大胆直接告诉全世界:“我们会消灭英格兰的!”
多么可怕的积怨。当德意志文明以一种弥散和强制的状态进行覆盖时,这些二十一二岁的热血青年都开始充当德国战车的履带一片。
今夜,英国队和德国队将在南非布隆方丹自由州球场,为世界杯8强席位进行生死决战。
德国人的心里,永远留栖着一个玫瑰色印记,这,属于英格兰。
作为欧洲舞台最富个性的两个国家,英德从血缘崛起、发展道路和性情经历上都出奇的相似。传统文化背景在欧洲大陆的滋长却完全由这两国激起相反的两面。一个是水平方向上的绝唱,一个是垂直方向上的呼喊。百年来,两次世界大战,英德都是直接对手,同样战得地球颤抖,这种战争和政治上的外因,早已发酵百年。
对历史来说,这就是杯苦酒。回到足球本身,英德恩怨,更加纠结。
1914年,当萨拉热窝事件宣告一战开始,英德的死敌状态以一种绵长的对峙呈现,圣诞节,思乡浓烈的英德官兵却心照不宣地停止了对抗,开始在各自战壕里举行庆祝活动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休战期间,双方更在“无人地带”进行了多场足球赛,其中一场比赛是由一名英军士兵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足球,在人数和时间均无限制的情况下开始了比赛。双方队员兴致盎然激战起来,直到比赛用球被铁丝网扎破泄气为止。此次比赛英军以3比2获胜,也成为最早的英德PK。
是PK,自然就血气方刚。1938年5月14日,英德在柏林进行友谊赛,当时希特勒正作为狂人叫嚣欧洲,英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,要求英格兰队员放水,不允许赢德国,可这些热血男儿,为理想、奋斗和爱,将所谓的政治要求砸入浸满血液的柏林土地,哐当当灌了德国6个球。飞机划过胜利的天空,英格兰在德国的床单上留下了一部永垂不朽的电影,《胜利大逃亡》……
贝利、史泰龙是主演,英格兰那帮逃跑的疯子,则是史诗。
多年后的1966年,英德又在世界杯的举办权上展开争夺,英格兰人又一次击败德国人,国际足联选择了现代足球的发源地,作为庆祝英足总百年华诞的贺礼。天意弄人,1966世界杯决赛,也就是在英德之间展开,率先取得进球的德国人并没有笑到最后,英格兰前锋赫斯特的帽子戏法让雷米特杯有了第5个主人。
那一年,英国默瑟蒂德菲尔附近的威尔士采煤村庄阿伯方发生倒塌悲剧,147个孩子,整整一代都不存在了。“阿伯方”悲剧直接导致英格兰10万人集体喷泪,那长长的集体葬礼甚至也引得德国媒体的关注,“整个欧洲都是忧郁的。”
仇恨,因为更大的悲剧而萃取出巨大的感伤。这些感伤,却在凝固后成为更大的仇恨。当赫斯特当年所谓的“门线球”成为千古悬案后,英德恩怨上升到空前的层面。欺骗与被欺骗、傲慢与偏见、癫狂与沉郁……这枚玫瑰色的伤痕深嵌心骨。
4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上,德国人终于迎来了报仇的机会。1970年6月14日,英德在1/4决赛相遇。当场比赛,卫冕冠军英格兰队取得了2球的领先,然而坚韧不拔的德国人并未放弃抵抗,在常规时间内扳平了比分。第108分钟,“轰炸机”盖德·穆勒攻入制胜球,完成逆转。
那一年,英国世界级的哲学家罗素逝世。这是欧洲“原本文化”的重大损失。英格兰人的德国观,就是希特勒和集中营。耿耿于怀,挥之不去。二战、柏林墙树立、政治对立、经济互掐……在双方多次修补外交关系的努力中,都收效甚微。
柏林墙倒塌的意义,更大层面是精神领域的互相试探,英德恩怨的分量,却并未因墙倒而消散。
人们希望的是足球让战争和分歧走开,却没想到更加迷乱。
上世纪90年代,点球决胜成为双方恩怨的关键词。1990年,我们记住了加斯科因的眼泪;1996年,双手叉腰、昂首踏步的德国人安迪·穆勒又成为传奇。2002年韩日世界杯预选赛,英格兰队5比1狂胜德国队,创造了两队交战史上最大分差———“恩怨”,成为英德的姓名。
这,属于一群孩子的年少轻狂。
- 拉里昂达被同伴害惨:结束世界杯之旅 难逃球迷声讨 2010-6-28 14:49
- 世界杯“移民”横行 首发11人9人竟不会唱国歌! 2010-6-28 14:46
- 网友世界杯4场进球彩:荷兰大比分取胜 日本突围 2010-6-28 14:42
- 巴西拿智利祭刀 世界杯两队预选赛一幕将重演? 2010-6-28 14:40
- 切尔西巨匠注定悲情谢幕 世界杯上他就没有得分的命! 2010-6-28 14:38
- 英格兰队长耻辱方式告别 杰拉德:这是我最后的世界杯 2010-6-28 14:35
- 工藤:“英德大战”激情四射 两大豪强胜败有凭 2010-6-28 14:34
- 新闻晚报:错判 南非世界杯的标签 2010-6-28 14:23
- 每日新报:这就是经典 英德对决成就世界杯之美丽 2010-6-28 14:22